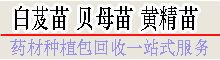曾經有一位富有同情心的觀察者,通過艱苦的努力,得到了關于人吃人的第一手資料。阿芝臺克人從市場上購買奴隸,把他們養胖,“這樣可以使奴隸的肉更有滋味。”
其其麥加山谷是“人肉的埋葬之敵”。據說南美的圖皮南巴族會將他們的敵人“吃到最后一片指甲”。漢斯·斯塔登的暢銷小說中,描寫了在1550年前后他被食人族所捕獲,由于食人族的盛宴祭祀儀式被一再拖后,使小說的情節變得令人窒息、毛骨悚然。他對食人儀式的描述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受難者必須忍受女人們的嘲弄,要自己點燃篝火,而他將在火上被燒煮。人們重擊他的頭,腦漿噴濺在地。然后女人們徹底剝掉他的皮,把他的身體弄得很白,并用木塊抵住他的肛門,這樣就不會遺失任何東西了。然后一個男人……將他的胳膊和膝蓋以上的部分砍下來。
四個女人將切好的部分抬走,圍著茅屋奔跑、狂歡……內臟部分由女人們保管,她們把內臟煮熟,做成名為“明戈“的濃湯,供她們和孩子飲用。她們吃掉腸子和頭上的肉。大腦、舌頭和其他可以吃的部位都給孩子們吃。當這些全部做完之后,她們就帶著自己得到的肉回家了……當時我在現場,一切都是我的親眼所見。
在本世紀末期,西奧多·德·布雷在其膾炙人口的美洲旅行小說中,栩栩如生地刻畫了食人族哄烤人的四肢、女人們喝人血、吃內臟的情景。在十七世紀,類似的記載并不多,因為人們對此感到十分恐懼,沒有發現新的食人族和吃人風俗。
然而,到了十八世紀,由于有更多人遭遇過食人族,歐洲人重新對此發生了興趣,哲學家們紛紛想借此說明奴隸制度的高尚性。歐洲人想象,在高度文明的基督教國家埃塞俄比亞,仍然存在著專門販賣人肉的屠夫。在十八世紀北美洲的印地安戰爭中,一個馬薩諸塞的民兵驚恐地發現,他們的對手“以最令人感到恐怖的速度”煎烤著敵人。
當雄心勃勃的探險家探索南海時,發現了更多人吃人的例子。在十八世紀的很多故事中,都記錄了美拉尼西亞的食人族,他們看來是最實際的部族了:將俘獲的敵人全部吃掉,絲毫也不浪費,骨頭磨成針,用來縫制帆布。當庫克船長首次遇到毛利人,他們比手劃腳地教他如何剔凈人骨。
他的描述在歐洲受到質疑,其代價就是葬送了更多人的生命。關于斐濟食人族的記載,與十九世紀早期歐洲傳教士的敘述很相近,但是,由于其規模龐大,已經發展成為一種常規儀式,背離了任何文化意義,“并非只是恐怖的報復行為”,正如衛理公會派教徒在1836年所斷言的,“而是成為對人肉的純粹的喜愛。”